文/陈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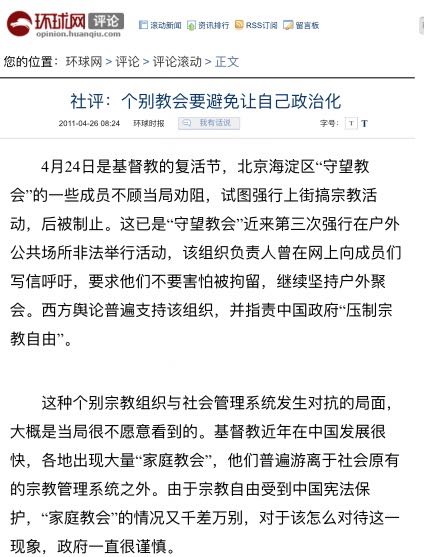
初次结识守望,居然是通过《环球时报》。我第一次知道“守望教会”这个词,是通过媒体知道的:2011年的一天,我上网的时候看到了《环球时报》的那篇社评。当我看完那篇社评的时候,我当时的感受有两点:一是充满好奇。当时我尚未归信,以我对《环球时报》的印象,我倾向于教会。但我很好奇,守望教会是一个什么组织?二是心生敬意。从那篇所谓社评来看,我当时知道的信息是教会因为信仰的缘故户外敬拜,因此我对守望教会萌生了尊敬,并误以为守望教会里面的成员都是神学家。就这样,那篇社评让我对守望教会产生了好感以及距离感。回想起来,上帝的工作妙不可言。也许,当时我上网只是为了看八卦新闻。
年轻人喜欢上网,“无独有偶”这个词已经不足以形容我与守望的缘分了,虽然信主之后,我尽量避免使用“缘分”这个概念。同样,又是因为上网,我加入了我们大学校友群。在群里,我结识了一位校友,她说她是基督徒,在守望聚会。我当时心想:“怎么可能?别逗了。”通过校友群,我又与一位同专业的师姐取得了联系。后来看到她分享了一篇“文化守望”公众号里面的文章,才得知她也是基督徒,并且委身守望。后来,在她的帮助下,2013年,我来到了当时位于惠新西街的杏花二组。初次来到小组的时候,我作为一名慕道友,没有觉得不适应,大概是因为当时我已经开始了解基督信仰以及阅读相关的书籍,并且第一次跟着唱赞美诗的时候,我也能照着谱子跟唱,一切都很自然,只是当时有两点好奇:原来教会里的聚会,不同于世界里的聚餐,没有互赠名片、攀比身份地位,有的是互吐衷肠、分享祷告事项;我们称呼祂为“上帝”,还是“主”、“神”?是不是称之为“上帝”显得更“高端”一些?就这样,我开始了接触和融入守望。

在这期间,我上了启发课程,当时是郭鹏程弟兄带领的。启发课程的最后一次的营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晓峰牧师。当时,我与晓峰牧师以及另一位慕道友安排在同一个房间,那个房间只有两张床位,有一个人晚上睡觉需要睡在地上。峰牧说:“那就我睡地上吧。”这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在2013年的时候,我阅读到了一篇对我影响较大的讲章,题名是《我信教会》,是袁灵传道在一次圣餐聚会上的分享。读过之后,我明白:天上的教会是得胜的教会,地上的教会是争战的教会。在那年,我学习了受洗课程,并于2013年年底受洗成为基督徒。在受洗课上,我第一次见到袁灵传道,之前我一直以为这个名字应该是一位姊妹。2014年的时候,我决定去zrx服侍,服侍之前需要通过师母的面试。我的面试在世人开来是失败的,因为之前没有见过师母,也因为特殊的原因,无法使用手机取得联系,结果我竟让她在麦当劳里面等了一个小时,而同时我在麦当劳外面等,直到她出来问我,我才恍然大悟。进去聊的时候,我想已经让她等了这么久,我肯定不会面试成功,于是我就天马行空地敞开了聊,简直是在“翱翔”。我说我喜欢唱歌,师母问我赞美诗唱得怎么样,我竟回答“唱得不怎么样,我通俗歌曲倒是会唱不少”。但没想到,我竟然面试成功了。这次面试,是我所经历的最意外的面试,不同于世界上的任何一家企业机构。
说起来到守望的日子,“户外”这个词是无法回避的。我第一次知道守望,也是因为户外敬拜受到了《环球时报》的社评。在上启发课程的时候,我询问鹏程弟兄、大宇弟兄以及虎兰姊妹关于户外的事情,他们告诉我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的确对此有不同的观点,并且跟我说了平台位置以及警车会停在那里。由于户外敬拜的初期,我还没有加入守望,于是我又上网了解了之前的一些情况。从我所侧面了解的那些印证来看,建堂和户外是出于神的。于是经过祷告后,我决定去平台敬拜。那几次派出所的经历,我印象也很深刻。有一次,我从派出所出来,已经是23点多了。当时袁灵传道在外面陪伴,他几乎一天都站在了外面,他跟我说:“太晚了,如果不方便坐车回家,可以去我家。”我感到有弟兄姊妹在外面陪伴是特别温暖的,使我一下子忘记了派出所里面的铁椅子以及个别警察的恶语相加。在户外敬拜参与陪伴的时候,有一次我与弟兄姊妹们交谈,好智弟兄说:“一琨小组那次的活动是这样的……”我感到很惊讶,因为信主之前我新浪微博上就关注过黄一琨,但我当时不知道他是守望教会的会友。于是我打断好智:“等会儿!哪个一琨?”估计我当时的惊讶表情是很夸张的。好智说:“就,就那个一琨啊……”。于是我内心感慨,上帝使用网络,让我总是提前遇到守望教会的弟兄姊妹。
从网络知道守望、在陪伴期间结识到弟兄姊妹、思考家庭教会与三自教会的区别,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守望教会的户外敬拜所引发的。以上记忆的碎片,我相信是上帝的预定,而无论我是软弱还是刚强,上文提到的袁灵的那篇讲章题目便是我的观点:我信教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