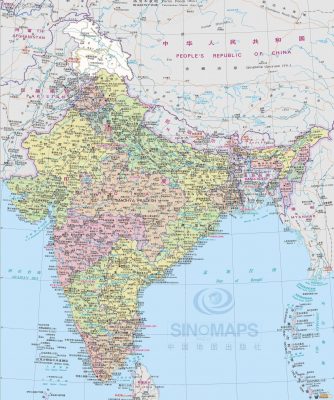信主,有时候想想还是挺奇怪的。初接触传道者的时候我一直耿耿于怀:为什么上帝狭隘到只救信祂的人?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个问题突然就不是问题了,或者直接说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又似乎被很巧妙地避开了这个问题,站在这个问题的旁边看着这个问题,感到有点神奇,神奇于怎么就会有这么一个问题,神奇于怎么就突然可以没有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我当初是多么地侃侃而谈于“没有哪个传道者能解释到让我满意”,我是多么地自傲啊!
大概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如春风化雨、暖阳释雪、和风拂面,不知不觉地将我浸染,将一粒上帝的种子播撒到我心里,慢慢地生根发芽、成长茂盛。这就是生命,一个有生命的圣徒暖暖地传递给了我生命,催发了我的生命。让我有了根、有了终点、有了归依、有了盼望、有了灵性、有了寻找的结束、有了真理、有了力量、有了光明。传道,用生命唤醒生命的方式,也许是最基础、最有效、最直接、最简单、最真实、最爱人如己、最必不可少且怎么绕都绕不开的传道方式了。
初到“启发”就途说道听了多人聚集有风险的说法。终于,我说出“为什么不将观念和思想明确出来、统一指挥、团结一心呢”?终于我说出“为什么他们就不理解一个几乎有完整生态、完全能独立生存下去的教会,能为中国和其他国家及民族祷告,顺应权柄的行为是多么地应当受到尊重”啊?到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我的内心因恐惧而向理性向集体要依赖要依靠要安全感;到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我的内心因恐惧、无助和无奈,而对“势力”的妥协。
当周围有生命的圣徒们,若无其事、泰然自若、甚至如战士如勇士般,用技术用智慧用勇气用信念支撑起作为一个基督徒所必须的聚会、传道、读经、祷告的天空时,不断有零星的消息是关于锡安教会、秋雨圣约教会,以及我的弟兄姊妹们被逼迫的消息传进我的耳朵;当我在思考有没有一个中间地带既不违背信仰又能被政府理解的问题的时候,有在国外待过的圣徒告诉我说:“即便是美国,也会有基督徒被压逼的情况”。于是我有点明白了,有点“理解”政府了;当我开始抱怨和愤青于政府的愚昧无知,思考上帝给基督徒的福分和当下面临的逼迫,有信徒告诉我说:“这是大浪淘沙,上帝在借着政府如筛子一般在拣选和试炼稗子与麦子,这不能用属世的眼光看,这也无所谓好与不好,并且自古以来基督徒都受逼迫,这是常态。”也有圣徒说“事实上证明福音越逼迫就越兴旺,感谢主”,甚至有圣徒祷告说“不知道是应当求上帝保守还是求上帝试炼,但求上帝给那些正在受逼迫甚至在监的弟兄姊妹以力量”,我还听到说“受到逼迫,挺过去后,与没受到逼迫的是绝对不一样的”,当然还听到牧师说“上帝的作为就是为了基督徒的,哪怕是今天刮风了,思路也应该是:这肯定与教会有关系”,于是,我也开始向上帝诉说我的意志,也与上帝说“希望知道上帝的意志”。
但是,我还在思考需要神迹,因为人的意志何等软弱,人是何等不靠谱的呀?倘若没有神的特别看顾,哪里会受得了那些“有经验的土匪”的严刑拷打或简单的用灯照着让你不得休息,失去时间概念,意识模糊,意志崩塌呢?当然,有人说,只要信,在哪里都一样,我并不反对这句话,但是,如果就仅仅是以政府的意志为转移,恐怕就不是上帝所喜悦的,同时,会被一步步控制,被魔鬼的权柄所颠覆。
我积极地准备着那“不测”的一天,问东问西、问有经验的弟兄姊妹们,以形成应对“套路”。当一位弟兄针对我的担心说“有教会,决不会让你露宿街头”的时候,当我总结“可以零口供;要温柔、要忍耐、不可血气;站在神国的位置给属世的他们传福音并爱他们;可以事实求是地说出信主带给自己的生命改变;不当签的材料绝不要签;要第一时间求弟兄姊妹们代祷;可以适当地以对方之矛攻对方之盾。”当我发到群里并对那位弟兄说“我准备好了,找我也不怕”的时候,上帝就给了我信心:我能承受的。
那天上班中接到了一个陌生的手机号的通话,面对每一个陌生号我都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思考一番,终于这个电话没让我失望,说是居委会的,想找我聊聊,问我啥时候有时间。电话里是女声,言语间有点涩,态度软和。她没说什么事,我也没问,算一种心照不宣了。我回答中午、晚上都可以,并说了上下班时间。她对于中午这个时间有点客套似地说影响我休息,言词间闪闪烁烁,但当时紧张地如临大敌的我并没听出她的底气不足、心虚胆怯、言不由衷来,于是我就约了下午下班的时间。
有姊妹说可以直接回绝而不和她谈,此话甚是可行。一方面她也是上派下干,应付差事、不得已而为之;另一方面她也是个人,无论是不是“官面”的,她也一样处在交际技巧里,意即如果我交际或说处理人际极佳应该是极有可能对付得了她的。此处的她可指一切这个性质的人。我没有这么做是因为我觉得心里面并不怕她,我觉得既然是光明正大的、既然是同处世间的、既然早晚都要面对,就有必要谈谈、有必要交流,有点来者不拒的意思。
现在想来,我有点太“爱”她们了。我曾画过一张三个方框套着的图发群里,表达的意思是最外层是神的国的范围,包括着里面的一层也就是教会的范围,然后又包括着一层才是政权的范围,中间一个点是人。基于着这种包容、爱和温柔的“高高在上”的姿态,我对她们用的是外柔内刚,以柔克刚的策略。也许我说的也没有错,也许没有对与错,全看个人实力如何怎么控制结果了。但是,其实我是一个相当没有嘴、不会交际的人,只会说客观的道理和事实,而基本搞不清人情是什么。以后的事实证明,我这种不善应付人际的人,这么海纳百川的来者不拒是相当愚蠢的;以后的事实证明,我这样“精心”的准备真是准备的太“完整”了,以至于把自己套里面了,《圣经》说:“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马太福音10:19-20)
她并没有按约定在下班后再谈,而是打完电话不久就来了。在找另一位姊妹谈话未果后,我就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我们院的党委书记兼后勤院长打来的,这是位曾经当过武警的湖北人,这是“党的人”。他客气地问我是否有时间到小会议室一趟,有点事儿。这事儿当然就是和居委会的她谈话的事儿。这个她终于用了这招:即直接联系行政职位在我之上的人,而且还是“党的人”,这应该是被那姊妹激愤起来的缘故。居委会的人,哪怕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尤其是年龄偏大的女人,约等于家庭妇女,面对一批至少她认为对方有点墨水且较她年轻的人,还是不那么有自信的。
我终于在小会议室见到了她。我在到会议室之前,按照所准备的在几个小群里发了求代祷的信息。此时的我虽然心里忐忑、腿肚子有点发酸,但是,果然感觉到背后那“义人的力量”,越走近会议室脚步反而越坚定了些,当我看到她的身边并没有公安的时候,我的紧张感就缓和了些,但在那一刻我心里是有一丝丝失望的。说起来这种感觉比较奇怪。
那通知我去的“党的人”轻轻带上门离开了。我坐到了她的对面,中间隔着长条桌子,桌上放着她的包,摆的样子让我联想到里面有个摄像机。这促使我做了录音这一行为。她是一个略矮、略胖、不算黑的大于45岁的妇女,神态恭谨。她似乎不知道怎么开口,不知道从何谈起?我很直接地说知道她为何而来,我说自己是信上帝的,这与共产党的不相信有神直接是相反的;我说信了主后使我光明很多,远离了杂念邪淫,心里平安,这对社会是有正面意义的;我说我也是有判断力的,也是读过书的,也是有职业的,并不是思维错乱、迷信无知的人。
而她并不能反驳我说的话,似乎对这个信仰的领域比较陌生,似乎从没想到信仰还可以有这样的作用,这可能和她平时所想的迷信式说辞并不一样。所以难以招架的她只反复说着一句话,似乎只有这句话是她唯一准备的、唯一能想到的话,那就是“你也许是不明内理,被蒙敝了,既然党国对此有意见,那么党国就是对的。”然后,终于干巴巴地拿出一张纸,是A4纸,只有3到4行的样子,占了那纸的约1/6,这种排版显得瘦弱无力,内容是:“姓名(身份证号)承诺不参加守望教会的一切活动。”到后来我知道其实那身份证号是19位数,也就是多一位数,这应该属她们的失误吧。我对此的回答是:既然说守望是非法的,既然从来没承认过守望教会,又哪来的纸上的“守望教会”?我是不会签的。我的语气一直比较温柔。
这时候那“党的人”进来了,并没有坐下,只是很小心很官方地说:不要参与这些,我曾经参与过镇压这类的非法活动,会很惨的,年轻轻的不要参与这些。然后我重复了一下自己的立场,并直接说(虽然我说的温柔但态度是鲜明的、立场是坚定的):“我是不会签的。”她说是看在“党的人”面子上没有叫公安来,但是如果不签就会和公安再来。我表示不惊讶且非常理解。她和“党的人”说,这承诺书留下,意思是让“党的人”说服我并签字。
这整个谈话过程中,无所适从、不知所措的她就是为了应付上面的任务硬着头皮来的,看得出她对上面是绝对服从的,是有决心完成的。也许上面下的是死命令吧。我对这次的谈话比较满意,对方抛来的问题我都给推回去了,也没有透露任何的关于教会的信息,我觉得至少可以暂告一段落了。——其实这次的谈话我并没有将守望和信仰区分开来,我有点偷换概念的意思。
几天之后。“党的人”拿着承诺书直接找到我,并顾忌对我的影响,在一个无人的房间和我重复了那天他所说的话,并强调居委会又给他打电话了,责令他让我签字。我明确地说这个是不会签的。他没有任何的强迫,但将纸留下了并说让我三思,我当时想他将纸留下了是不是他就有种扔了烫手山芋的感觉?最后他说让我把另一张承诺书给那位姊妹,我当然没答应,因为这并不是我的事情。我就是在这张最后成了我开会时的应急记录纸上,发现那身份证号其实是错的。此纸在我后来搬家的时候感觉很有点可笑但不失纪念意义,于是我没有当垃圾扔掉。
在以后的几天里,和这位“党的人”碰到过几次。只有一次他又提起这事来,说这是件严肃的事,不签是不会完的,会没完没了。他的表情很僵硬,似笑非笑,似乎预备着我的强硬反驳而不自然地肌肉痉挛。可是,我并没有针对他,只是表达了对这事的理解。
在被下次约谈之前,在主日学发生的一件事让我不能忘怀:轮到我们组带领敬拜了,时值一人感冒一人回老家,也就只剩下我了,临时抱佛脚,匆忙准备后开始当天的敬拜,奇怪的是中途几度要流眼泪,几度满胸的话语不吐不快,却又一言难尽,当时有段经文是耶稣上十架的,于是我借着这经文说了面对逼迫的现状,强调了尽量态度温柔、立场坚定的话,求主赐下圣灵照看我们,主的试炼必不超出我们能承受的。
就在我以为我的应对策略很正确的时候。主日后的第三天,一次让我终身难忘的谈话来了,冲洗了我自以为正确的认知。
那天上午,我接到“党的人”的电话,说下午下班后有点事要谈一下。他没说什么事,我也没问什么事,我就直接答应了。快到下班的一段时间里,我猜测肯定还是和“信仰”有关的事,并和同事托出这件事的大概,同事表示此事甚难理解,难道信仰不是自由的吗?一边聊天一边吃饭的时候,“党的人”来叫我,并对我先来吃饭感到诧异。“党的人”领着我走向谈话地点,等在门外的她问我同事是和我一起的吗?同事赶紧说不是,在以后的相处中,在只言片语之间,同事都在往一个方向努力——敝清和我的关系,尤其是宗教信仰方面。
这次的谈话是在一间诊室。“党的人”用钥匙打开门后闪身让我进去,这才发现里面有12双眼睛,这包括1个丰台堂的男性张牧师,1个丰台统战部的女部长,西局派出所的人,还有跟着我进来的居委会的她,一共6个人,三男三女。在居委会的她介绍了那统战部部长后,那部长与我握手,然后介绍了其他几个人,态度客气谨慎,但我并没有能对号入座哪个人是哪个部门的哪个职位。之后,“党的人”叫后勤的人买了农夫山泉送进来,当然“党的人”把我叫来后自始至终就没进过这间房的门。主谈的是那女部长,开门见山说就是谈谈信仰的事,目的是了解一下而已,可以畅所欲言。女部长坐在门诊大夫坐的位置,我坐在病人会坐的位置,女部长对面是位男性,一言不发闷头做笔录。女部长后面是丰台堂张牧师,侧面是一男一女,居委会的她坐在靠近门的位置。自始至终,这居委会的一共没说几句,就是表示一下自己是和统战部一条线的。另外一位女性说了几句话挑明我话的可能的含义,其他的几人除那牧师外就没说一句话。
女部长从“信仰自由,守望非法”入手,开始是侃侃而谈,后来就转圈,也不说想让我签字或者想让我干什么,我主动摆明了不会签那上次居委会拿来的承诺书。女部长不断地强调我是被蒙蔽的,不断地试探我在哪聚会,不断地说共产党政权的正常和威力,不断地表现出对我职位、籍贯、甚至对信仰的看法等信息的了解,不断地说可以去丰台堂敬拜,不断地说我们可以成为朋友,不断地透露出会请求牧师祷告、会让牧师帮国家代祷等不反对神的意思,不断地说出比如“受洗”的字眼,以表明自己懂得基督教信仰。我不语。这女部长就一圈圈地将说过的话又转一遍,完全没有要结束谈话的意思,我终于感觉到厌烦了。但是,我对这女部长说的信仰自由没法反驳,对守望非法、我被蒙蔽的这种双方都无力证实和证伪的说法感到争论无益,于是直接回答,这是由共产党定的,党说是黑就是黑说白就是白,当然,这些人还是说国家的权威和我被蒙蔽。于是我被逼到面对一个问题:去不去丰台堂?我的回答是:可以去。当时我在想,之前就去过,我答应可以去的话就象征性地去一下就得了,不算撒谎也不算违背承诺,此时丰台堂的张牧师顺着那统战部长的话开始表态了,他说:听讲道一定要听正统,不能听邪道,比如有的教会讲成功之道就是不对的。然后诸多的比如,这种说法是自说自话、偏离实际、完全是在给统战部拍马却还不想得罪我,故一再说:“我是比如啊,不是说你们教会。”到此,我说了几句守望教会讲道的正统性和深度。
我觉得此牧师简直就是自欺欺人、糊里糊涂,无法再和他交谈,因为我的胃的确是开始不断的痉挛,似乎要吐出来了;统战部的终于说别去守望了,我回答说不会签的,统战部的说不签也可以,既然是信徒,就算个口头承诺吧!此时的我被逼到了退无可退。因为我无法再用“你们既然不承认守望又何必担心我去守望”的字句了,因为我回答说是在“北京受洗的,是在教会受洗的,是在这个教会受洗的,是在守望教会受洗的”;因为我回答了可以去丰台堂看看就得面对不要去守望聚会的问题。最终我选择了一个回答:你们都不给守望地方聚会,我又能去哪儿聚会呢?统战部的说能承诺不去海淀聚会吗?我只好做了一个当时认为很聪明但之后追悔莫及失落到晚上睡不着觉的回答:我可以不去大恒聚会。
此时的我的心理活动是:既然都没给钥匙,想进又哪能进的去呢?——从头至尾,我的准备在指导着我的思路,这种准备让本来就没有应变之才的我更加没有及时调整策略,而是惯性地在按着当初的设定走,但其实这次自大的我并没有发给弟兄姊妹们代祷信息,其实我确实做到了没签字、做到了温柔,做到了貌似不违背神的话语,其实我输了,输给了这个统战部的人,输给了这属世的人。我其实等于一直想在一个灰色地带求生存,既不想违背神的话,又不想与政府有尖锐的矛盾,于是我选择了文字游戏,选择了温柔对待,选择了只表明自己的立场,其实我哪怕是缄口不语都好得多。因为我张口玩的这文字游戏,这不说谎话,这种灵巧很难表达出心中所想而让自己心怀愧疚,同时这种偷机取巧,无论对自己在逻辑上是否留下了余地,都会被对方认为自己已经被他们驯服了。更重要的是也许统战部真的在摸底:摸摸守望的圣徒们对守望的坚守力量有多大,以此来确定是否要取缔。试想如果各位圣徒都像我这样圆滑,那统战部还能感觉到那股守卫守望教会的力量吗?那他们能不得寸进尺吗?其实事后我知道,尤其是统战部的人是在“前锋”居委会那里得到了我的想法,甚至我的说话内容和我的样子,他们做了精心的准备,是一步步迂回把我绕进去的。
所以说,靠着神去胜过他们是必须的,这并不是说要血气,可以简明扼要地表明立场后不说话,不必对他们客气,不必对他们委曲求全,不必可怜他们,甚至不必理解他们,一定要把自己放到鲜明的立场上交出去,要靠着圣灵活出神的生命,叫他们不敢践踏信仰底线,因此望而生畏退避三舍才行,这才是对神的荣耀,而不是去一味的爱他们、理解他们、可怜他们、迎合他们、不能在他们面前卑微,不能在他们面前讲忍耐,如果让他们无理还挑三分,一步步占领高峰缩紧包围圈,到那时候,不对的也变成对了,那些自己不屑说的话可能会变成哑巴口中的黄连,到最后也说不出了。
其实一开始我以为他们不懂、不理解我们,其实不是的,他们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他们想的根本就是自己的政治,哪管我们到底是对还是错?我以为他们蠢,其实是我蠢,他们想的和我想的根本不是一个水平,想的对象也不同。他们既然是在搞自己的政治斗争,那么,有时候我也会想,也许他们是在应付差事,是我们太不给他们面子,太往枪口上撞了,也许他们留下了让我们继续下去的路径,是我们太较真了。
政治我是不懂的,也不知道我最后的这个猜测对还是不对。我们跟着上帝走,我们是公开的基督徒,不与任何政治做斗争,可是也知道政治不会不与我们做斗争!我们跟着“脚前的灯”走下去,传扬神的道,希望神的国降临,希望世间被光明透亮和净化,也希望为中国的教会和圣徒争取到哪怕一点点权益,但同时也知道这的确很难!我们是应该以被逼迫为荣,还是也可以稍稍考虑下教会的出路在哪里呢?
就在被谈话后的第三天,也就是周六晚上的时候,我又被“党的人”打电话问是否在宿舍?能不能再和居委会的人谈谈?我说可以,周一吧!结果,在挂掉电话的30分钟内,我宿舍的门就被民警、协警、保安、居委会的约十几个人敲开了。民警执意要往宿舍里走,不肯出去谈,并开始挑宿舍的毛病:比如接线板不合理等等。居委会的人给我留下了“取缔书”,同时留下了两个保安蹲守在门口,一直到周一早上我上班后才撤去。在这期间幸亏有弟兄智慧的话语安慰我。
周一晚上,“党的人”趾高气昂地说:“要不是我认识居委会的人替你挡着,你就麻烦了。”我无语,他告诉我“不签的话,是会没完没了得找的”。一直到有一天,院办突然找我谈话,在场的果然有“党的人”,直言不讳地说因为上面的压力不能再和我合作了。我没有反驳,冷笑了两声,同意解除合同。